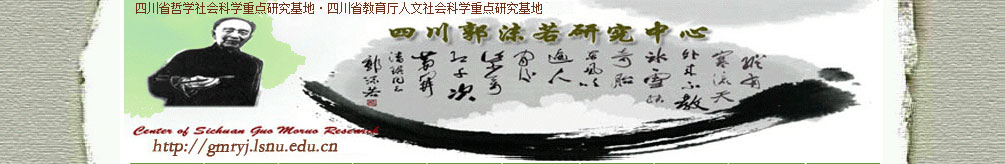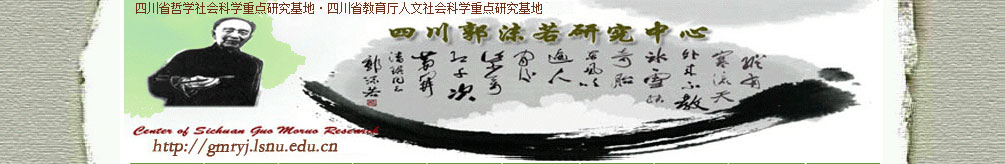我要说的话
周恩来
在朋友中间,在文坛上,通常喜欢将鲁迅和郭沫若相提并论。这原是一件好事,而且是应当做的事,可是有时候也成为多事。多事就是将无作有,将小作大,张冠李戴,歪曲事实,甚至分门别户,发展成为偏向,这便不应该了。
要并论鲁迅和郭沫若,我以为首先要弄明两人的时代背景和两人的经历,是多少有些不同的。
鲁迅的时代,是一半满清,一半民国的时代。他出身于破产的士大夫家庭,他受过封建社会很深的洗礼,他受过戊戌政变后的洋务教育,嗣后,留学东洋,又受教于章太炎先生,并参加了光复会。入民国后,他又做过多年北方官僚社会的小京官,也可说是闲差事。直到“五四”的前夜,他才得参加思想革命的运动,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骨干。从此以后,他就公开的成为宗法社会的逆子,士大夫阶级的叛徒,逐渐养成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,可是他自己却又那样谦诚的愿意做一个“革命军马前卒”。瞿秋白同志说得好:“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,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到……群众的真正友人,以至于战士,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,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,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。”(瞿秋白:鲁迅杂感选集序言)所以毛泽东同志说:“鲁迅的方向,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。”蔡孑民先生也说:“为新文化开山的,在周豫才先生,即鲁迅先生。”(蔡元培:鲁迅先生全集序)鲁迅所努力的,拿他自己的话来说,就是:“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,肩住了黑暗的闸门,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,……”(鲁迅:坟)这就是鲁迅为大众而牺牲的精神。他自己愿做“桥梁中的一木一石”(同前),其实他就是这过渡时代的伟大的桥梁。
郭沫若的时代,却稍为异样了。他虽在少年时代,也是关在四川宗法社会里面的,但是二十岁以后,他走出夔门,几乎成为无羁绊的自由知识分子了,虽然他也如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,过着贫困和流浪的生活。他的半商半读的家庭,虽也给他一些影响,但是三十年来大时代所给予他的影响,却有着异常不同的比重。就拿经历来说,他既没有在满清时代做过事,也没有在北洋政府下任过职,一出手他就已经在“五四”前后。他的创作生活,是同着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,他的事业发端,是从“五四”运动中孕育出来的。我们不能把郭沫若看成是前一辈子的人,而应看成是我们这一辈子的人,虽然他比鲁迅也不过只小了十一岁。我们也不能把郭沫若看成是两个时代的人物,而应看成是新文化时代的人物,虽然他在少年时代也曾舞文弄墨过一番。
因此,我说: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,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。鲁迅自称是“革命军马前卒”,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。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,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。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,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。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,他的遗范尚存,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,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,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。
从这样观点出发,自然在并论鲁迅和郭沫若的时候,便不会发生不必要和不应有的牵连和误会了。
鲁迅先生在思想斗争和新文化运动上之非常可宝贵的革命传统,秋白同志在《鲁迅杂感选集序言》中已经指出四点:第一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,第二是“韧”的战斗,第三是反自由主义,第四是反虚伪的精神。这都是非常之对的。我在这里不想再多说了。要说的是郭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二十五年当中,所给予我的印象和我所认识的特点是些什么?
第一是丰富的革命热情。郭先生是革命的诗人,同时,又是革命的战士。他心中笔下充满着革命的愤火,也充满着对于人类的热爱。当“五四”觉醒时期,当创造社草创时期,他的革命热情的奔放,自然还带着很浓厚的浪漫谛克,这正是当时知识青年的典型代表。但是经过前一次大革命炉火的锻炼,经过十年海外的研究生活,他的革命热情已经受了革命理智的规范,然而他内在的革命烈火,却决没有消失,相反的,愈蕴藏便愈丰富。一旦抗战号响,他便奔回祖国,他的革命热情,也就重新爆发出来了。四年多抗战,不论在他的著作上,在他的行动上,都可看出郭沫若仍然是充满着革命热力,保有着当年热情的郭沫若。可是时代究竟不同了,客观的事实不断的教训着我们充满了革命热情的郭先生,于是郭先生有时竟沉默起来了,革命的现实主义久已代替了革命的浪漫谛克主义,郭先生已到“炉火纯青”的时候了。
第二是深邃的研究精神。有人说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不能兼而为之,其实这在中国也是过时代的话,郭先生就是兼而为之的人。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,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,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,埋头研究,补充自己,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,准备了新的力量。他的海外十年,充分证明这一真理。十年内,他的译著之富,人所难及。他精研古代社会,甲骨文字,殷周青铜器铭文,两周金文以及古代铭刻等等,用科学的方法,发现了古代许多真实。这是一种新的努力,也是革命的努力,虽然有些论据,还值得推敲。如果说,连卢那察尔斯基都不免在退潮时期入了迷路,那我们的郭先生却正确的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的研究的道路。现在的郭先生似乎又清闲了,恰好为纪念他的二十五年创作生活,大家主张集资建立沫若研究所,我想这是最好不过的事。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,指导这一代青年,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,以充实自己,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,郭先生,现在是时候了。
第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。郭先生是富于战斗性的,不仅在北伐、抗战两个伟大的时代,郭先生是站在战斗的前线,号召全国军民,反对北洋军阀,反对日本强盗和逆伪的;便在二十五年的文化生活中,郭先生也常常以斗士的姿态出现的。正因为这样,他才能成为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。也正因为这样,初期创造社才能为革命文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,才影响了后期创造社在思想意识上的一些论争。自然后期创造社的争论已多少表现着“文人的小集团主义”(秋白语)。可是鲁迅先生也说:“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,是他们‘挤’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,明白了先前的文艺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问题,……以救正我——还因我而及于别人——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。”(三闲集序言)同时,这里必须为周郭两先生辨白的,他们在北伐期中,谁都没有“文化相轻”的意思,而且还有“同声相应,同气相求”的事实。周先生在《两地书》(69)中明说“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,也想到广州后,……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,造一条战线,更向旧社会进攻,我再勉力写些文章。”在广州发表的文学家宣言,周郭两先生均列了名的。广州事件后,郭先生曾邀鲁迅先生参加创造刊物,列名发表宣言,不幸因新从日本归来的分子的反对联合,遂致合而复分,引起了后来数年两种倾向斗争的发展。这从“切磋”的观点上看来,未尝不是一件有收获的事,但是,因此而引起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无聊的纠葛,一直影响到鲁迅晚年时候的争论,那真是不应该的了。有人说,鲁迅先生“韧”性的战斗多表现在他的著作上,郭先生的战斗性,多表现在他的政治生活上,我想,这种分法,并不尽当的。因为一个人的战斗性是发源于他的思想性格和素养的,文字和行为,不过是他的表现的方面罢了,并不能说这是差别的所在。真正的差别是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,较任何人都持久,都有恒,这是连郭先生都会感到要加以发扬的。
这些,也就是郭先生在革命的文化生活中最值得提出的三点,也就是最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三点。
我这不是故意要将鲁迅拿来与郭沫若并论,而是要说明鲁迅是鲁迅,郭沫若是郭沫若,“各人自有千秋”。
鲁迅先生死了,鲁迅的方向就是大家的方向。郭沫若先生今尚健在,五十岁仅仅半百,决不能称老,抗战需要他的热情研究和战斗,他的前途还很远大,光明也正照耀着他。我祝他前进,永远的前进,更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!
民国卅年十一月十六日晨